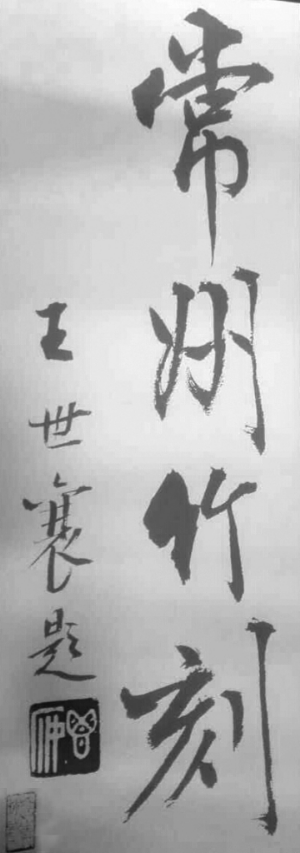|
2008年秋,我致信曾在常州博物馆供职的文博专家陈晶先生,建议她写一篇有关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与常州竹刻的文章。来年春天,陈晶先生撰写的《王世襄与常州竹刻》一文刊于上海文汇报,文章称:“在明清时期,江南竹刻素以嘉定、金陵两派称著,常州在历史上并非江南竹刻中心。半个世纪以来,常州如何异军突起地走出了一批留青竹刻名家,并传承了明代刻竹人张希黄的留青竹刻一脉,王世襄先生对此鼎力扶持,真是功不可没。” 王世襄先生文革期间从“牛棚”出来后,就着手整理其舅父金西厓的《刻竹小言》,并自费油印,赠送给有关爱好刻竹的人士。金西厓是我国近现代竹刻艺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著名竹刻艺术大师,一生作品与著作颇丰,《刻竹小言》初稿成于1948年。然就在王世襄先生整理刊印《刻竹小言》之时,全国范围内还在从事竹刻的艺人已寥若晨星,倒是常州还有二三人埋头其间,其中又数前辈白士风先生成就最高。于是,常州竹刻自然而然吸引了日本、香港、台湾等地藏家的目光和订单。那时我正在刻鸟笼,是香港人订的货。我欲求进一步提高竹刻艺术,便到处苦苦寻找竹刻资料,有幸搞到了王世襄先生的油印小册子,细细研读,方恍然知道竹刻还有这样大的艺术世界。欣喜之余又无奈不能亲眼看到臂搁、笔筒等竹刻作品的实物,哪怕是照片等资料。 作为当代竹刻艺术的鉴赏、评论权威,王世襄先生竭尽全力呼吁抢救传承竹刻艺术这项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嘉定竹刻”闻名遐迩,可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就逐渐衰落,以至绝响。粉碎“四人帮”后,为恢复嘉定竹刻,中兴竹刻艺术,王老专门找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希望他关心嘉定竹刻。胡厥老是嘉定人,早就有此心愿,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嘉定竹刻”,还把自己收藏的竹刻捐给了嘉定博物馆。嘉定博物馆腾出房子,开设竹刻讲习,并给予从业者政策优惠。嘉定方面多次来常拜访白士风先生,后来,也几番找我交流技艺。我应邀数次去嘉定,但我因耳背,难为人师,也不愿为人师,就把他们介绍给徐秉方先生。徐先生曾多次到嘉定指导,搞出了成绩。嘉定博物馆竹刻工作室环境清雅,墙上醒目地挂着胡厥老“嘉定竹刻”的墨宝,以及嘉定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嘉定竹刻工作室”的招牌。嘉定还成立了竹刻博物馆,王世襄先生题写了匾额。刻竹艺人的待遇也不错,刻竹费时费工,为使刻竹的人安心从艺,政府每月给予补助,作品可以自己处理。当地政府对竹刻这样重视,让我看了非常羡慕。 后来,我在无锡看到“双契轩”竹刻工作室挂着一块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篆书的匾额。无锡“双契轩”由常州名人所题,这让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我曾到过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三楼看到很多竹刻包装盒都印有“常州留青竹刻”字样,我故意问:“竹刻是哪地方出的?”回答道:“是常州的,常州竹刻世界上很有名气的……”是的,常州竹刻并不落后,王世襄先生说过,当今留青竹刻的中心在常州。为什么没有名人为常州竹刻题书呢? 我渴望有名家为常州竹刻落墨。常州人文荟萃,不缺名人,却不知找谁写好。那时刘海粟大师的名气如雷贯耳,一字难求。为常州竹刻题字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关乎常州文化的大事。我辗转找到乡贤钱小山先生,欲通过钱老先生请海老题写“常州竹刻”,钱老大笑,说海老太忙,其时又身在海外。此路不通,只得另辟蹊径——请王世襄先生,遂于1998年去信求王老写。王老说我写不好,但后来还是写了,并说“写得不好,就不要用”。我不懂书法,但感到王老的字很硬朗,笔力扛鼎,典型的文人学者书法(见图)。 王老很看重白士风先生,白先生曾经是全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竹刻老前辈。上世纪90年代白先生已归道山,为常州竹刻艺术的一大损失,考虑到先生留下的一些竹刻拓片日后可能会整理出版,那将是常州竹刻艺术文化的重要传承,我便又索求王老写《白士风竹刻集》的书封签条。王老得知白先生走了很是伤感,写就了一竖一横两帧签条书法,于1997年2月初寄给了我,并希望出版后寄他一本,惜书直到目前仍杳无音信,这是一个永远的痛。 如今,竹刻艺术已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老人亦已仙逝。睹物思人,每每看到王老的题字,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D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