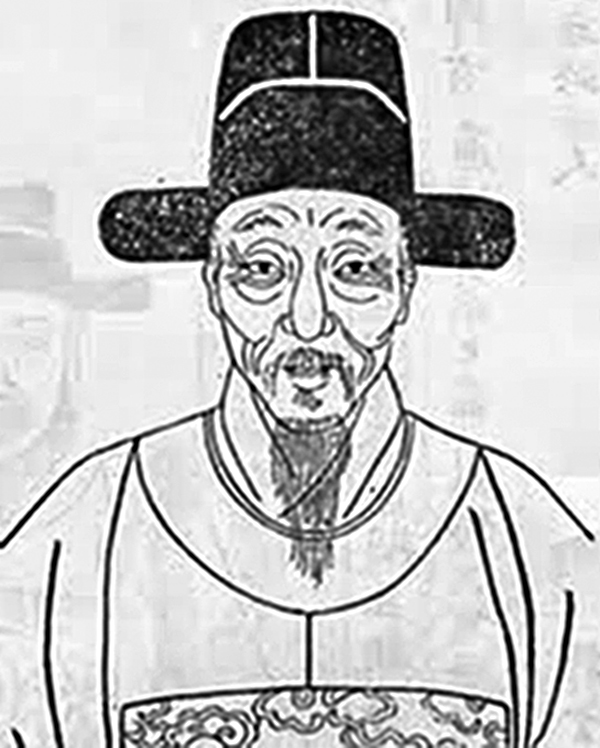常州青果古巷·名人篇·唐鹤征
时间:2012-08-15 10:16来源:人文常州网 作者:包立本 邵玉健
唐鹤征,1538年生,字元卿,号凝庵,常州城区人。明代末年思想家、方志学家。其为明代文学家、抗倭英雄唐顺之的儿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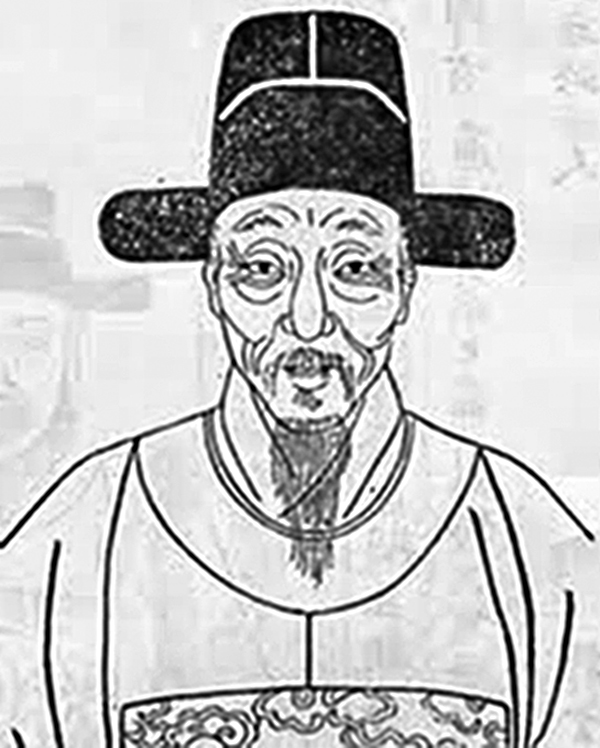
唐鹤征,1538年生,字元卿,号凝庵,常州城区人。明代末年思想家、方志学家。其为明代文学家、抗倭英雄唐顺之的儿子。其故居位于天宁区青果巷中段北侧的“唐氏八宅”之一的贞和堂、四并堂,易书堂等,西与晋陵中路相邻,东连刘国钧故居,南近周有光旧居。他在编撰的《武进县志》中评价自己:“少豪爽负气,不能卑伦侪俗,随人俯仰。或以势凌之,有头璧俱碎耳。早失怙恃,几为人所鱼肉,强,不致陨越。年二十九,受教于应城李先生,始闻危微下霁之论,稍涤其习气,未能尽除也。”隆庆元年(1567)赴江南乡试中举人。隆庆五年(1571)参加京师会试又考中进士。先任礼部主事,但因与当朝宰相张居正观点不合,内心颇浮躁,感到前景渺茫。直到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其一派倒台,他的仕途方顺畅起来。历任工部郎、尚宝司丞、尚宝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等职。任太常寺少卿时,曾请以陈献章从祀孔庙。因屡次上书陈事,受人妒忌,托病归里。他自言:“盖生平所志,不在禄厚,亦不愿居功名。第冀少抒谋议,因机决策,转败为功,袺然长揖归田,其愿毕矣。”后来曾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
唐氏自九流百家、天文地理、稗官野史,无不究极,其学渊源于王守仁之学,属于南中王门,但又不尽同于王学。他作为唐顺之的儿子,其学术思想受父亲之影响较大,黄宗羲谓其学“得之龙溪(王畿)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关于宇宙本原问题,他提出了“乾元生三子”的理论: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生于乾元,天地亦生于乾元,故并称之曰“三才”。从而否定了“天能生人”的传统说法。“乾元”是“气”的别名,“盈天地之间,一气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极也,太和也,皆气之别名也。自其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非气外别有理也”,“知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则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气”。可见,“乾元”不是抽象的精神本体,而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这种“气本论”的思源于张载,鹤征曾谓“盈天地间,只有一气,唯横渠先生知之”。唐氏的心性之说,也较有特色。他认为,心不过是五脏之心,舍五脏之外无心,“心之官本思”,“心与行非有二也,自其浑含谓之心,自其运旋谓之行,唯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运旋不息”。心的妙处在“方寸之虚”,是容纳“性”的宅所。此“方寸之虚,实与太虚同体,故凡太虚之所包涵,吾心无不备焉,是心之灵即性也”,舍心,则性无所于宅;舍性,则心不得而灵。在认识论方面,唐氏强调“自得”和“悟”。认为君子深造之道,舍自得别无出路;欲自得,舍悟别无得路。“悟”虽为禅宗术语,但他对“悟”的解释不同于以往心学,提出“彼谓一悟便一了百当,真圣门中第一罪业也”。他主张“悟”要在学习中进行,学应该“日有孳孳,死而后已”。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知不能脱离行而独立存在,没有即等于没有知,特别重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主张“知易行难”。唐氏受道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曾运用老、庄学说的某些理论解说《周易》,其中含有一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如认为事物都是永恒运动变化的,矛盾的对立面是相互转化的,等等。唐氏对孟子提出的养气之说表示赞赏,以为所谓理、性、神都是气之最清处,养气就是要养得清明之气。他对“格物致知”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认为“知”是“良知”,但不同意王守仁以心、意、知为物而格之的说法,也不同意朱熹的事事物而格之的主张,提出将“格”训为“格式”,即法则,“格物”就是要使物物皆得其则。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慎独”,即慎干一念未发之前。唐鹤征名义上属南中王门学派,但他是从王学中分化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力图纠正王学末流的弊病。其心性说为“从来言心者所不及”,在宋、明、清思想发展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他著有《桃溪札记》、《周易象义》、《周易合义》、《皇明辅世编》、《宪世编》、《太常遗著常州府志人物志》、《太常遗著》、《武进县志》、《南游记》、《元卿三稿》等。万历年间的《重修常州府志》序载:“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七月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两京太常寺少卿郡人唐鹤征撰”。另有学者考证《北游记》、《南华正训》为其作,唐鹤征并修正了《西游记》,陈元、唐光禄、华阳洞天主人都是唐鹤征。1617年八月,正值唐鹤征八十寿辰,孙慎行书匾为寿,并作了《保合堂记》,记述了保合堂(贞和堂前名)的来历 ,下署“万历四十五年八月日之五赐进士及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印信编纂起居管理诰敕 愚甥孙慎行顿首拜撰”。两年后的1619年,唐鹤征在青果巷家中病逝。(文/包立本 邵玉健)
(责任编辑:DY) |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