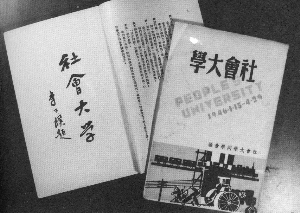|
李公朴和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金明德/供图)
话说1930年底,李公朴从美国回到可爱的祖国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当时中国官僚社会的一个缩影。李公朴在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糜烂腐朽的官僚政治生活使他感到窒息,他立志“誓不为官”。为此,他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但在南京,有一个是他最留恋也是最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李公朴说:“那里是他最能畅开呼吸的地方。”实事求是说,他完全是冲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去的,在这里他俩无话不谈,亲如兄弟,自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2年春,李公朴回到上海开展社会教育,他和正在上海组织发起“科学下嫁”活动的好友陶行知畅谈了好几次,每次谈到教育,他俩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赞成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观点,他对陶行知先生说:“你着眼于学校教育,在学校里把学生教育培养好。我致力于社会教育,把社会青少年的教育抓起来。”陶行知很赞成李公朴创办“流通图书馆”,向青少年提供适合他们的各种书籍。最后在上海地下党,亲朋好友如黄炎培、邹韬奋,特别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李公朴成功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从此,李公朴有了一块进步的、坚固的思想文化阵地。 李公朴在巡视各校时,一有机会就上台演讲,大讲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理论。高兴时还给同学们讲陶行知改名字的故事:陶行知原名叫陶知行,因在实践中认识到实践出真知,“行”比“知”更重要,故而改名。由此进一步向同学们指出:“看一个人的好与坏,革命与不革命,爱国与不爱国,不是听他的知﹙言﹚,而要看他的行。”李公朴讲得诙谐风趣,同学们听得为之动容。 1933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文化界进行残酷大围剿。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思想专制,由蔡元培领衔,李公朴和陶行知、黄炎培等学术界100余人,冲破禁令,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活动。当晚李公朴撰写了纪念大会的报道,刊登在《申报》显著版面上。据说蒋介石在南京看了这个报道,大大地“生了一回气”,把手中的杯子狠狠地砸在地上,责骂上海市公安局长“娘希匹,都是吃干饭的”。 1935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李公朴和陶行知双双被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李公朴和陶行知参加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李公朴和陶行知一起谈论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问题,陶行知写了这样一段话:“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惟其不惑,所以不忧,所以不惧。吾辈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送给李公朴先生,李公朴用毛笔书写成条幅,两人互相勉励,以“三不”的态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1945年10月1日,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陶行知和李公朴又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民盟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职务…… 在日后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李公朴和陶行知两人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感情也越来越深。最后发展到在重庆共同创办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他俩共同确定“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这一教育方针;共同商量“‘教、学、做、用’合一的行动教育”方法。重庆社会大学类似延安的“鲁艺”、“陕公”等学校,这样新型的、进步的大学,必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扼杀的对象。但是,李公朴终身从事民主教育的决心没有动摇。他和陶行知临别时相约,将来回到上海、北平,一定要继续办好社会大学,完成他们的夙愿。 社会大学同学会为了纪念这所大学,编印了《社会大学》一书,内容有陶行知、李公朴的讲话、文章和诗歌等。李公朴还在初离开重庆前为《社会大学》写了序言。但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批邮包寄到昆明时正是1946年7月12日,就是李公朴光荣牺牲的那一天。半个月后,陶行知在上海因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突患脑溢血,不幸逝世。这一本为了纪念社会大学的校刊,谁也料想不到竟成了哀悼李公朴、陶行知两位先生的纪念会刊。 (责任编辑:D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