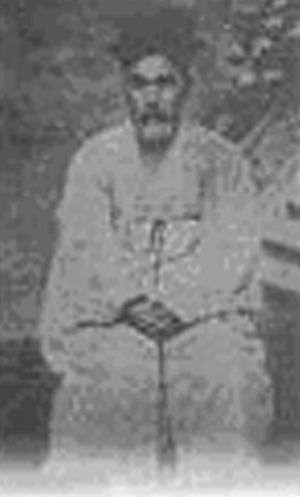|
有清一代,常州地方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一批学者出走乡邦,或谋一教席传道授业解惑,或持续深造砥砺学术造诣,对推动常州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大有助益。清末民初,中国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日益繁盛,常州籍史学家屠寄(1856年-1921年,光绪朝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国史馆总纂等职)在执掌南通国文专修馆期间,与流亡中国的韩国学者金泽荣因学术交流结成深厚友谊,成就了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交往之缘起 金泽荣(1850年-1927年),字于霖,号沧江,朝鲜京畿道开城郡人。1891年,年届42岁的金氏中进士后,一直为政府从事历史编纂工作。1905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乙已保护条约》,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金泽荣不甘当亡国奴,决心效仿明朝遗民朱舜水反清兵败逃至日本,流亡中国。因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南通张謇1883年出使朝鲜期间与他有过数面之缘,意气相投,金氏便于1905年秋携家人乘船赴沪投奔张謇。张謇和胞兄张詧为金泽荣在南通租赁一屋,并安排其到翰墨林印书局承担编校工作。 20世纪初,张謇在南通倡办新式教育,翰墨林印书局即为通州师范学校编印教材所设的印刷出版机构。1908年,张氏又开办南通国文专修馆,“专为养成社会办事书记之才”而设,因屠寄曾任清末封疆大吏张之洞、端方等人幕僚,十分熟悉当时公文事务,便被聘为馆长。屠寄、金泽荣同在南通张謇处就职,最初之交往发生于1911年6月。当时,屠寄为所撰《蒙兀儿史记》搜集旧集和外文史料。他慕名去金泽荣处借书,读到金的诗稿,赞赏有加。当得知金因手头拮据无力刊印时,屠当即表示要出资给予支持。不仅如此,屠寄离开南通张詧为其饯行时,屠说:“请以所为饯者为醵,则吾不饮而已醉矣。”张詧素敬重金泽荣,“笑而应之,自巳至酉所醵金凡七十有奇”。金泽荣自选诗文集《沧江稿》很快在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他在序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列出屠寄、张詧等38位捐资者的姓名。 重逢在常州 1911年6月屠寄离开南通前与金泽荣的短暂交往略显仓促,而后来金专程来常州看望屠,则是两人交谊之延续和深化。屠寄对金泽荣之来访感到十分欣喜,当即书联一副:“思君不来怀闲素,何日痛饮开兰衿”,并旁书:“沧江老友积年不晤,顷来又不能久留,与订后约,当过平原原定之日数,方畅也。”在常期间,屠寄携众多文人与金泽荣酌酒赋诗,遍访史迹,极尽欢愉之情。短短数日,他们访问了苏东坡、唐荆川故居,并赴盛宣怀妻弟庄茂之家赏菊。金泽荣向来仰慕中国传统文化,年轻时即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文章中领略了唐宋派散文的雄奇精妙,后来又称自己为文喜好韩愈、苏轼、归有光,为诗喜好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因长期推崇苏轼之诗文,苏东坡故居也就成为必到之处,而且他专门作诗“十八日赴屠归甫招至常州明日同归甫观苏东坡古宅”。 金泽荣在常逗留时间不长,但旧友重逢,十分欢悦,竟写下了“同屠敬山赴庄茂之菊花大会之招”、“杂赠常州同游”、“将归南通留赠归甫”等10余首诗。屠金两人在常州的重逢,使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为笃厚。以至于后来金泽荣在南通得知屠寄逝世,悲痛地写下挽诗:“当年倾盖乐新知,况是牙琴值子期。惹得旁观惊欲倒,万宜楼上剧谈时。奎星匿彩玉扬灰,凶信闻来失酒杯。拙著伤心披不得,行间几处见魂回。”他在挽诗中把两人比作伯牙、子期,屠寄离世,金氏竟不忍翻书了。 共携吕思勉 常州籍史学家吕思勉因屠寄之引介,也在南通、常州两地与金泽荣成了忘年交。吕氏1884年2月出生于常州十字街,在求学道路上深受屠寄之影响。他早年即与朝鲜学者秋景球有所交往,但得识金泽荣亦赖张謇建立之国文专修馆。1910年1月至次年6月,吕思勉应屠寄之邀执教于该馆。1911年6月,吕跟随屠赴金泽荣就职之翰墨林印书局借书。当读到金氏诗有“四面星辰鸡动野,一江风雪马登舟”之句,吕盛赞其有唐诗之意境。金泽荣拙于汉语口语表达,但能熟练运用中文撰写,三人只好以笔谈方式交流。当谈到日本侵占朝鲜后,不惜摧毁民族文化,吕思勉问有何办法补救。金氏悲痛地写道:“非至其地,不能搜其书。”虽为初次见面,但三人感情融洽,临别时分别以诗相赠。 (责任编辑:D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