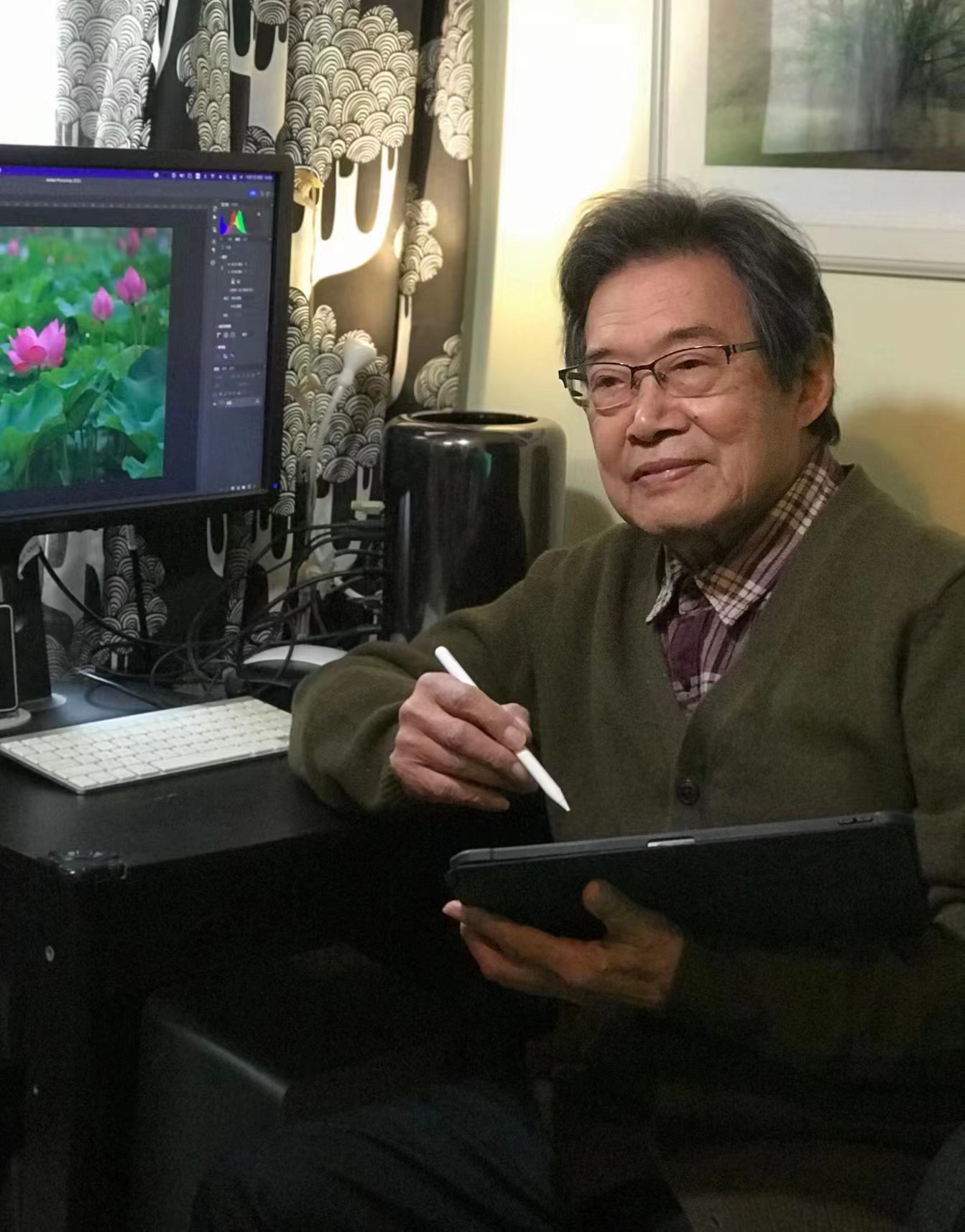 多年前,时任南京画院书记许怀华来常州市美术家协会调研时,指名要见吴锦渝,说吴锦渝是他在南京的同事、画友、好友,还戏称他绘画就是向吴锦渝学的。上世纪50年代时他们同在南京某军工企业工作,在工作之余大家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一同创作中国画,参加展览,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吴锦渝的祖父吴中行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画意派摄影代表人物。吴锦渝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艺术,自学绘画。在南京时,他得到傅抱石大师亲授。在南京市工人文化宫美术学习班,每周日上课时间,有亚明、宋文治等江苏画院大师来上课、指导。在工作后的业余时间,宿舍里同事们在打牌取乐玩耍,吴锦渝则盘坐在双人床上铺,腿上放着画板,拿着铅笔构思作品。吴锦渝创作了国画作品《假日下乡》《支农路上》等参加展览,得到好评,并在《新华日报》《雨花》《工人日报》上刊登。《工人日报》在画刊评论中介绍了他的作品。 连环画是少儿文史知识启蒙读物,深受群众喜爱。上世纪60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把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家庭问题》改编成连环画,物色到有工厂工作、生活经验的吴锦渝来绘画,吴锦渝接受了任务。傅抱石大师看了吴锦渝画的连环画稿后,勉励说:画树木不仅要画出各种树木的姿态,还要画出各种树木的性格,连环画主要是画各种人物的更要主注意这一点。大师的话一直是吴锦渝的座右铭。 60年代初,在南京总统府西花厅省国画院内,江苏人民出版社召开连环画创作会议,邀请上海、江苏等地的画家参加,吴锦渝是江苏为数不多受邀的画家。傅抱石等大师在会议上说:连环画集导演、人物、动作、背景等设计,不简单的。 《家庭问题》连环画文字改编者、作家殷志扬也是常州人,当时并不认识。殷志扬后调回常州文联工作,两人才相交恨晚,后殷志扬出版的文集又请吴锦渝配图。 一本连环画的出版要经过编辑、领导三番五次的审稿修改,最终定稿、印刷、出版发行,其中甘苦只有绘画者自知。《家庭问题》出版后,他拿到了400多元稿费,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及全家都很开心。祖父吴中行笑着说:有点像我呢。 当吴锦渝要调回常州市卫生系统搞宣教工作,时任南京市文化局长曹汶曾经挽留,说可以调他到南京文化单位作专职绘画宣传工作。 回常州后,家中人多拥挤,祖父吴中行特地在楼上靠窗位置放上书桌、书橱,供他创作用,并经常上楼观看他的作品,提些意见。 吴锦渝从60年代初创作《家庭问题》后,又给江苏人民出版社画了《红Y头》,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画了《买车》。成稿后送至出版社,并己通过审稿,即将付印,恰遇1966年运动开始而杳无音讯。 70年代,吴锦渝借调到常州市美术创作组,到省里参加创作会议,到江阴等地体验生活,领了《江防图》连环画创作任务,与好友是有福合作创作了连环画《江防图》,参加了全国美展,成为那个时期常州首次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并出版大开本外文版,参加国际书展,到国外展销。当时在南京外文书店,醒目地置放着《江防图》大开本外文版连环画。 后来他又出版了十几本连环画,有《岳飞》《敌后枪声》《虎穴设卡》等。有些获了奖。《敌后枪声》场景取材于常州,常州市摄影家协会领导唐锡勇一一翻着画稿说:这里是常州古城墙,这是旧文庙,这是大井头,这是文亨桥,这是北大街……真是一本常州味实足的绘画作品。那时他还创作了大幅国画《采药图》参展,获得赞誉。 80年代后期,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邀请吴锦渝绘画《呼家将的故事》,吴锦渝当时已任宣教科科长,负责美术、摄影工作,有时还要到区、县所属部门指导工作,所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他多次到图书馆、博物馆、书店寻找宋代资料,特别是受到宋人《清明上河图》的启发,把这些史料融合到绘画中。夏天点着蚊香防蚊叮咬,冬天怀中揣着中间是焦炭的小铝壳扁圆暖盒,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每天晚上绘画几小时。千军万马、排阵布列,人物动作,衣饰背景,蕴藏脑中,落笔如神,跃然纸上。1991年1月,《呼家将的故事》上中下三册出版。上册《血战伏虎山》、中册《会师卧龙寨》、下册《呼延庆挂帅》,每册120多页,还有彩色封面。出版社编辑表扬:画得细致。出版社后悔未出大开本的,大开本的效果会更好。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某领导要吴锦渝申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却迟迟未申请。 吴锦渝美术生涯中涉及品类比较多,还有装帧设计、壁画、雕塑、插图、摄影创作等。从70年代开始至今,吴锦渝参加了设在红梅公园的《收租院》泥塑群雕塑、椿桂苑的常州状元大型壁画、瞿秋白纪念馆壁画、东坡公园仰苏阁壁画、红梅公园北大门的四根梅花屏柱等设计,任《常州市爱国卫生展览》《中草药展览会》等的总体设计等,深得赞许。在南京宝船公园,有吴锦渝设计的《郑和下西洋》大型汉白玉浮雕5块,高约2.5米,其中最长的一块约有20米长,总长度约50米,展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恢宏场景。 吴锦渝为人诚恳,乐于助人。有了出版社的约稿,还邀约年轻人来合作,辅导他们。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原馆长张德俊经常说:“吴锦渝人非常好,好人有好报。”作家殷志扬说:“锦渝的画饱满、鲜明、精细、耐读,自有一种血肉肌理之感。更可贵的,是他努力追赶时代,永不满足自己的精神。” 文/田野 (责任编辑:DY)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