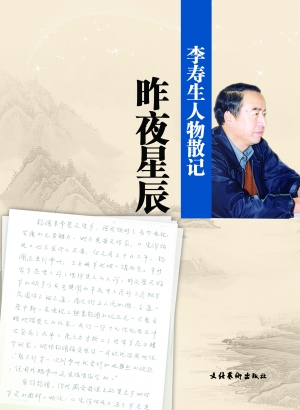|
李寿生先生是常州的老报人,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常州文艺界都很尊敬的一位老作家。他1964年当兵入伍,1965年起就在军内外报刊发表新闻作品。1970年退伍至省煤田地质勘探队,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又撰写了大量的诗歌与报道。1980年至2006年退休,他在常州日报干了整整26个年头。工作之余,又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连同这本人物散记,他先后出版了四部文学专著,其中散文集《我的乡村》还荣获了常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这在常州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中,乃翘楚也! 听说寿生青年时期是个写作的苦行僧。他在部队五年,一篇篇通讯报道和影评,不是在桌子上而是在床板上写就的。连部的办公室轮不到普通战士,食堂里又太嘈杂。他写报道,总是卷起垫被,在床板上铺上报纸,写下一篇又一篇习作。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宿舍,连队已经熄灯,他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写下自己一鳞半爪的观感。夏天,汗水湿透衣衫,湿透稿纸,仍挥汗不止。有一次,他在师部大礼堂后台看到一位新闻干事,吹着风扇在书写报道,寿生羡慕极了,他说:“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夏天写稿,也有一台风扇在旁边吹着。”他写的新闻报道,引起迟浩田等师部领导的关注。退伍前一年,他已被调至师部支左办公室和《无锡日报》(当时叫《红无锡报》)军管组工作。后终因家庭社会关系等问题未能入党提干。“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退伍回乡了。 1970年,寿生来到南京省煤田地质勘探队工作,之后又随队至苏鲁皖豫交界处搞野外勘探,他在钻井队工作好几年,跋山涉水家常饭,餐风露宿寻常事。每天下班之后,煤油灯下,又在铺板上摊开了稿纸,写下了一首首反映勘探生活的诗篇及通讯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新诗多次被新华日报、江苏文艺、南京日报、南京文艺刊用,成为我省小有名气的工农兵作者。写作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七十年代中期,他先后被调到省煤田地质勘探四队和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任宣传干事。1980年秋进入常州日报社,1990年起先后出任过常州日报、常州晚报的副刊部负责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寿生没有正规学历,他硬是靠艰辛的自学和写作走上文坛的,且学有所成。 人物通讯,人物特写,人物回忆录,我以为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应当为尊者违,掩着毛边说光边。更不能歪曲历史,妄涂油彩。寿生笔下的诸多人物,严守这一信条。写许世友,并没有回避他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如对杜方平等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写迟浩田,许多作者都回避他在苏州三支两军的这段历史,寿生敢于触及,实事求是地记叙了他在苏州市的文革岁月。写吴文英,更是一分为二,客观公正,既写她的高风亮节,也写她晚年的错误。写原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没有过多地对他的政绩进行臧否,而是以诸多细节写出了一个普通百姓眼中的杨晓堂,读来真切动人。我以为,人物传记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信史。惟有信史,方能使读者心悦诚服;惟有信史,方能传至后世。 《昨夜星辰》收集了一百位人物的一百十三篇散记,书中最大的亮色是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了这些名人艺人报人身上的正能量,谱写了一曲曲扣人心弦的正气歌。十年浩劫,原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身陷囹圄,他在狱中用豆酱作为黑色,把南瓜作为黄色,将辣酱作为红色,顽强学习画画,终成正果。文革结束后,他以一支画笔挣得的所有稿费和离休老干部的全部积蓄,支援沂蒙山区,打造了一所希望小学。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散文大家菡子,以顽强的毅力,与脑血栓展开搏斗,稍微恢复一点记忆,便躺在病榻上撑块硬板纸开始练笔,开头一天写不了几句,直至半年内写出了14篇散文。临终前居然完成了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的《菡子文集》。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蜚声文坛的文坛保尔王观泉,他是蘸着生命的泉水在写作。七年出了七本书,本本引起轰动。《郁达夫传》写毁了右眼,《瞿秋白传》又写毁了左眼。双目失明后,《陈独秀传》又在构思中。一曲曲正气歌,令人荡气回肠。 寿生的这本人物散记,采写的诸多风云人物,不仅写出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写出了他们叱咤风云的动人故事,而且写出了他们闪光的思想和不凡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譬如著名诗人、杂文家刘征谈讽刺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级党报党刊,能否发讽刺诗,究竟可以讽刺到什么程度,如何把握这个度,刘征说:其一,讽刺诗的繁荣只能说明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反之,讽刺诗就会走向死亡。因此,讽刺诗的发展,是好事,不是坏事。其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讽刺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作家心里应该有杆秤,如同妈妈指责孩子一样,要有分寸。注重社会效果,是作家起码的良心。其三,希望官方对于讽刺作品给予充分的理解。写讽刺作品的人大都也是老百姓,不一定每句话都是对的。刘征二十多年前的这些宏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D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