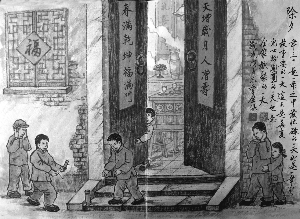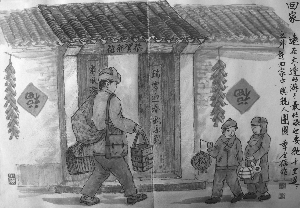|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孩子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最期盼、最开心的日子,莫过于过年了。因为一年到头埋藏在心底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都能在过年的时候得以实现。 穿新衣。逢年过节,每个家庭都要打扫卫生,清洁环境,自然也免不了给孩子打扮打扮。为节约起见,父母会在岁末将比较满意的裁缝师傅请上门来做上几天衣服。技艺好的裁缝师傅过年时很俏,生意红火,忙不过来,需要预约。在我刚能记事的两三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祖母到上海姑妈家去了,家里没有人手,母亲就在上班时将我领到东门牌楼弄口西面的一家裁缝店里看管,下班时再将我同回去。从这时起,我就有了 “裁缝做衣服”的概念。记得有一位夏姓的裁缝师傅,技艺尚可,效率较高,人也厚道,他是我母亲同事的先生,彼此关系较熟,我们的新衣好几年都是他做的。因为平时不懂得打扮自己,穿上新衣反倒觉得有点别扭,这是我告别开裆裤穿上瞒裆裤那年的特殊感觉,具体的年份已记不清了。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打扮意识的增强,过年穿新衣便就成为了一种内心的需要和外在的炫耀了。新衣一般做得较大,可以穿上两三年,因而有时过年就不做新衣了,只是将穿脏或穿破的衣裳缝补浆洗一下。穿上这样以旧代新的衣裳,心里总是不大愉快,尤其是看到条件稍好家庭孩子穿着新衣,心理就更不平衡了。有什么办法呢?父母只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理解。 放鞭炮。这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做的事情,意味着告别旧岁迎接新年。我家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清晨燃放炮仗,每次燃放8响。我们手拿玩具,躲在屋前,站在门口,捂着耳朵,眯着眼睛,瞧着父亲走到空旷处,将竖放在地上的炮仗慢慢点燃——嘣,只见炮仗向上穿越,啪——又在空中爆炸。成功啦,我们欢呼雀跃。这时,邻居们也在自家门口燃放鞭炮,往日的宁静被打破了,喧闹喜庆中散发的硫磺味道扑鼻而来,还真有点香呢! 饱口福。平时素食为主,吃荤较少,荤素不平衡,加之顽皮运动量大,消耗多。过年了,亏待了300多天的肠胃赶紧要恶补一下了。年前三四天,母亲忙着给家里做团子和馒头,这时我们刚好在寒假里,比较空闲,就围着母亲看热闹,不时还要乱插手,帮倒忙。母亲心灵手巧,做的团子个个精美闪亮,只只圆润丰满,打开笼盖,香气扑鼻,秀色可餐,大饱口福。过年忙吃的事情还真不少,炒生果,爆炒米,糟扣肉,做蛋卷,包馄饨,搓糖元,拆猪头……凡是与吃有关而又能办得到的,父母都会尽力满足孩子的需求,让我们吃个够,撑个饱,解个馋。大年夜是全家大团圆的日子,因而也显得最闹忙了。这天,父亲从店里借了一只100瓦的大灯泡回来吊在屋顶,亮得如同白昼。我们先是祭过祖宗,尔后一家祖孙三代外加宠养的阿咪,围坐在摆满各式菜肴的八仙桌旁,尽情地享用着母亲烹制艺术的成果,其味美美,其情浓浓,其乐融融。 走亲戚。探访亲朋好友,这是过年免不了的一桩事情。父亲出生在上海,常州亲戚很少;母亲诞生在本土,排行老二,兄弟姊妹有7个,外婆家就在商铺林立的常州最繁华的南大街中段的铁市巷里面。因此,逢年过节探访亲戚,外婆家是首到的。我家本来租住在西庙沟和成全巷,后来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搬到东门城郊接合的地方,即新建的纺织工人及其家属比较集中居住的和平新村。这里环境相对冷清,麦田、菜地、沟渠、河塘,还有一些工厂、农家村落分布在新村周围,乡村气息较为浓厚。到外婆家去就是到热闹的城里去白相,就是去感受市中心的繁华气氛和享受外婆家大家庭的亲情温暖。我们一般在大年初二去外婆家吃中饭,有时连晚饭。这天外婆家人气旺盛,从上海回来过年的大姨、三姨全家,在常州的娘舅、四姨、六姨、七姨全家,再加上外公外婆和我们全家,大大小小几十号人聚在一起,你说热闹不热闹!此外,我们还会利用过年的机会,到父母要好的同事朋友家去作客,偶然也会到上海城里、武进乡下的亲戚家走走。有来无往非礼也,父母每年也总会倾其所有,热情地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来聚聚。就这样,亲情、友情在你来我往中联结着,加深着,延续着。 (责任编辑:D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