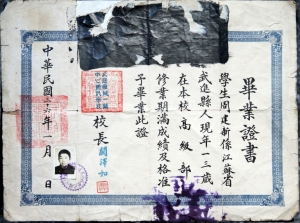|
我家四代人都是在觅渡桥小学读书的。父亲上学时校名为冠英小学。得益于在校练的珠算基本功,写得一手好字,他才在解放初期在食品公司当上了管理人员。我儿子和孙子也都是在觅小上的小学。1941年,我在觅小读书时,觅小的面积还不大,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约有20个教室,学生约千人,老师也不多,都在办公室集中备课。学校的基础课程是国语、算术、修身、体育、音乐、历史、地理、英语和劳作。学校里环境也不错,办公室前是个大天井,对面的墙壁处堆筑着假山,假山上有座师竹亭,旁边修竹数枝,别有风韵。 老师们个个热爱教育工作,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为我们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我们敬爱的班级老师,现在应该叫班主任的陈纯老师,她十分爱护我们,全心全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我们。记得教室旁有个夹墙,有天上早课时两位同学采用“搭墙”办法,把钱递过围墙买隔壁柏树头麻糕店的麻糕,买好麻糕他俩从窗口爬进教室时,陈老师已在窗口“接应”他们,把孩子扶进教室。这两位同学本以为免不了要受一顿斥责,却听到陈老师说,“学生上课要吃早饭,否则长期不吃会造成胃病。但是今后千万不要‘搭墙’了,实在不安全。”以后就没有同学这样做了。 陈老师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也在觅小上学,有一次他一人在西瀛里小水关桥那里碰到几个大烟鬼,面目狰狞,朝他招手舞脚,小孩子受了惊吓,不久竟一命归西了。陈老师十分悲痛,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同学们也很难过,深深地同情她,但她十分坚强,坚持上课,上课时根本看不出异常,可我们知道她的内心很悲苦。 教珠算的是一位男老师,他要求我们学好珠算,将来踏上社会会非常有用的。他对学生十分严格,处罚严厉。他将珠算乘除口诀和由斤求两、由两求斤的口诀要求同学背熟,还要练好手算,如果同学学不好,他就要惩罚,轻则立“壁角”,重则全班学生到操场头顶算盘站着晒太阳。不过,陈纯老师得到信息就会很快赶过来把同学们“彻底解放”。虽然当时同学们对珠算老师又“怕”又“恨”,可走上工作岗位后,终于体会到了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有不少同学名字难听,就起了一阵改名风,我也把名字改成“建新”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一位男老师,体育课的项目有跳远、跑步、双单杠等。学校每学期两次组织师生到电影院看电影,有次看美国的黑白电影《人猿泰山》,同学们回来后学着泰山的样子,手舞足蹈,大呼小叫。这时,体育老师就会出来制止。他会给我们讲些小故事,还说多少年后,“大家家里都能放电影的”。我们大眼瞪小眼,将信将疑,心里都认为老师是“瞎说八道”。后来事实证明体育老师是一位“预言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脑、电视,是不是“都能在家里放电影”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叫钱朴,她总是耐心教我们学新歌,当时正是抗战高潮时期,教了我们很多抗日歌曲,像《黄河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鼓舞着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读小学时,常州尚在“沦陷时期”,日本鬼子为了实现长久统治,进行文化侵略,强行规定学生要学日文。但老师们个个爱国,始终不上日语课。鬼子经常来学校监督察看,当鬼子由汉奸带领来学校检查时,老师早就得到通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日文课本,带着我们装模作样地读几句,鬼子看到还笑着翘翘大拇指。他们前脚走,我们后面就骂“八格亚鲁”。 那时,虽然孩子们的玩具没有现在多,却充满童趣:跳绳、滚铁环、踢毽子、搭洋片、抓雀子,还有官兵抓强盗等游戏。但我对那些活动都不太感兴趣,我的最爱是打乒乓。同学们的乒乓板都是用木板做的,乒乓台用两张八仙台拼起来。可是因为人人都想当擂主,不肯下台,大家就拼命拉台子,结果台子毁坏,乒乓也打不成了。于是我就改打篮球,篮球场就在觅渡桥对面西大街济美堂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内,篮架就架在两边墙角,篮球也用皮球代替,打起来也像模像样的,裁判也按照篮球规则,叫叫(哨子)一吹就开始比赛。等到正式球赛时,裁判还满嘴洋泾浜英语,起步叫“划沟”,传球叫“派斯”,暂停叫“推苗”等等。规则几乎与现在一样。学校每年还组织“远足”,现在叫旅游。我们出校门,过觅渡桥,走西直街,到西圈门,最后到西公墓,就散开自由活动。守墓人给我们讲种田的辛劳,讲粒粒皆辛苦、要节约粮食的道理。 (责任编辑:DY) |
|
|
|
|
|
|